- 邮政编码:404000
- 电话:023-58138448
- 墓园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天城镇茅谷村风水坝
- 电话:023-58413624
- E-mail:fsb_1998@aliyun.com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厚葬与孔子无关。中国人的厚葬制度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形成并相当完备,厚葬之风在商周时期已经达到第一个高潮,用人殉葬、用人祭祀的习俗曾经登峰造极。丧葬礼节的系统化和完整化,在周代已经基本完成。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厚葬高潮已近尾声。
中国丧葬习俗的演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原始社会时期,人死后像鸟兽一样不葬。在氏族公社时期,没有贫富,人人平等。丧葬极为简单:活人不忍见死者遗体腐败,盖上柴草,埋于野外,无坟无礼。这就是原始的土葬。自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以后,才有了埋葬亲人的习俗,并添加了殉葬品;后来又将柴草换成了棺木,殉葬品越来越丰富。在半坡遗址墓穴中,埋葬的死人多是头西,表示灵魂寄托西方的意思。这种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先的崇拜观念,在我国母系氏族时期就产生了。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厚葬之风和迷信活动更加盛行,奴隶主阶级为利用宗教迷信维持其统治。大力提倡厚葬,甚至把奴隶也作为殉葬品掉,作为祭品杀掉。商周时期制定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庄子·天下》)的葬制,天子、诸侯、大夫、士及一般奴隶主死了,在硷、殡、祭上,从时间、仪式、棺撑到殉葬品都有等级区分,而奴隶则只“举而委之加,或被当殉葬品活活埋掉,或像牲口一样被杀掉充当祭品。如古侯家庄发现的大墓,棺室雕饰纹,摆满了珍贵服饰器物;掉的外面排放着商王时期的兵器和手执仪仗器物的奴隶、男女侍从奴隶,还有儿童、宠物狗猴等。像这样的大墓殉葬、祭祀一般要杀气四百个奴隶。这种奢华、浪费、残酷的杀葬陪葬令人发指。春秋以后,人殉人祭不再是普现象,但一直并未彻底废除。后来,因为出现辨认先人墓地的需求,墓地起土堆(坟)才开始兴起。秦汉以后就几乎是无墓不起坟了。孔子葬母时,封土(坟)的造型已有若干种,孔子选取了斧形。由于中国宗法制度的发展,人们有了家族的观念,祖坟成了本家族的源头、最高偶像物之一,乃至成为后人赖以兴旺发达的精神寄托所在。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很多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但存在,还变成了鬼。比如墨子就说:“鬼神之有,岂可疑哉!”(《墨子·明鬼》)起先人们不知道这鬼有什么本领,后来渐渐觉得这鬼似乎是万能的,既害怕它作祟于生者,又希望它保佑生者,因而万万得罪不起。墨子认为:“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道家老前辈列子居然也相信鬼的存在:“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属天清则散,属地浊而聚。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列子·天瑞》)活人的精神,死后离开肉体就是鬼,鬼有自己的去处。所以,人们要不惜花费重金去讨好死者,祭鬼祭祖。这样,生者无愧,死者欣慰。正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隆厚葬之习经久不衰。孔子本人一般是不谈鬼神的,他只用心研究“为人”之“礼”,并不分心于鬼神的思考。他要求学生对鬼神敬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祭(祖)如(祖)在,祭神如神在。”一次,孔子病重,子路请求为他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似并没用),拒绝了子路的请求。(《论语》)孔子似乎在委婉地告诉学生:我不知道鬼神在不在,我权当它们是在的吧,恭恭敬敬地对待它们,不要寄希望于它们,尤其千万不要得罪,万一它们在呢?尽管我也不太相信。就是用教训的口吻一再教导孔子的老腆先生也不能改变孔子对统治阶级及其礼制和对生死鬼神的小L谨慎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说厚葬与孔子无关,似乎又有点说不过去。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怎么能说厚葬之风盛行与儒家的这个老祖宗没一点关系呢?
孔子传承并发展了古今之礼仪,把孝道与对父母的丧葬、守孝之礼紧密结合并传承了下来。此后,中国传统的儒家丧葬礼仪在后世统治者的引领倡导下更加完善。这种儒家丧葬礼仪形式隆重繁琐,等级森严,其基本程序据统计有三十二项之多。秦汉时期,坟丘墓得以保存,“陵”逐渐兴起,棺停制度进一步发展,墓上建筑和陵园规划制度进一步完善,更加丰富了丧葬礼仪的内涵。自此,中国丧葬礼仪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确立下来,中国后代王朝对此都很重视。随着儒学地位的确立,儒家提倡并执行的三年之丧制度也得到推广、沿袭。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殡葬活动中始终大量使用着濡家丧葬礼仪形式,贯穿着儒家所倡导的“孝道”精神。
儒家孝道文化强调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死如事生”,并将它提高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社会治理高度(《论语))。由于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对哀子顺孙的行为积极表彰,“孝”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夸耀的荣誉感,而在行“孝”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人们把表现孝道的方式与崇尚奢侈浪费的风气结合到了一起,错误地或者说片面地认为“孝”就是要在丧葬祭祀中用丰富的物质形式和隆重而繁缚的丧葬礼仪来体现。这样,儒家的孝道观就为中国社会崇尚丧葬,乃至逐渐演变为隆丧厚葬提供了一种堂而皇之的理论根据,也正因为如此,《淮南子·把论训》也说:“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
事实上,秦汉以后每一朝代的隆丧厚葬之风都与皇室的推波助澜分不开。秦始皇陵、汉武帝及其后的诸汉陵.唐宋及后代帝王陵绝大多数都是隆丧厚葬的典型。朝廷还依照规定向某些死者赠送物品。如果某个大臣有意行薄葬的话,朝廷也一定不予支持。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遗命薄葬.他的儿子们很想遵从.可是皇帝女婿不同意,以朝廷的名义踢给梁商漂亮的棺材、银缕玉衣等二十八种物品,钱、帛若+;女儿皇后也赏踢无数。((后汉书·梁商传》)上行下效,互相攀比,死者的子孙岂能小气?又岂能“不孝”?统治者自己隆丧厚葬,视死如生、孝亲是其厚葬的理由.待他人的丧葬自然不能走另一条路子,许多有条件的人都会竞相效仿统治者。唐代丧葬一度出现过度排场的状况,终致出现类似于齐桓公时的限葬令、限祭令,凡超出规定的丧葬、祭祀都要对相关人员予以严厉惩处。
统治者不仅是隆丧厚葬的带头人,而且是火葬的限挠者。佛教进人我国后,很多信佛之人采取了火葬。火葬本是一种节俭的丧葬方式,但是它和统治者倡导的孝道文化相抵触。唐律专设<残害死尸》条文,规定若焚烧、肢解尸体,照斗杀罪减一等,而斗杀罪轻则流重则死邢;若毁坏尊长尸体,则照斗杀罪处刑,那就会有杀身之祸。((唐律疏义》卷十八)宋太祖建隆三年下令禁止火葬:“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愈典礼,自今宜禁之。”(《续通典·礼典》)可是百姓中依然有人我行我素,比如山西人.他们还将骨灰撒于水中。南宋时民间火葬有愈演愈烈之势,屡禁不止。(顾炎武,《日知录·火葬》)明太祖也曾严令禁止火葬.给违反者治以重罪。清朝同治时法律规定不许毁坏亲尸,违者处死。为了解决穷人的丧葬用地间题,北宋起就有了漏泽园,就是在国有土地上设置乱葬场,无处下葬的尸体均可葬于此处。虽然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火葬的盛行,然而大量的佛教丧葬礼仪却还是与儒家丧葬礼仪逐步混合普遍使用起来。
儒家的殡葬伦理思想显然只是后人隆丧厚葬的理由或借口而已,因此把濡家的殡葬伦理思想简单地认定为隆丧厚葬的罪魁祸首显然是不科学的。
仪式、音乐都是一种象征符号
首先,要想确定仪式和音乐是一种象征符号,首先要明自什么是象征符号。象征一般是指非语言的符号表达活动。其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具有形象的实物;其二,它有代表作用,即它本身代表或表示另一事物。符号,用通俗的意义来理解即是人类为了把复杂的事物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了符号。符号学奠基人查尔斯将符号分为三类:类像、标志、象征。它们分别具有“相似性”(即感觉上相似的像类物)、“关联性”(即与被标志实物存在某种因果联系)和“规约性”(即与象征事物之间没有本质的相似或关联,而是依靠事先规定或约定的关系来代。由于象征具有了一般符号的功能,象征符号一词常被连用。
仪式,是一种超常态行为,它只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甚至特定人群中出现。它所存在的情境是在仪式参与者精神空间的虚拟世界。所以,仪式对于仪式参与者来说具有精神领域的意义()例如佛教仪式中教徒们跪拜的佛像、用来祭拜的香烛等物件,其本身都是没有意义存在的。只是人的观念加诸其中,认为佛像是佛祖的化身,焚香祷告就能让佛祖聆听到自己的心声等。这些行为和行动中使用的物件都是具有象征性的。因此,薛艺兵认为,仪式中的任何行为、现象和物件,只要它超出自身的本义而代表其他事物或含有其他意义,都可以成为仪式的象征符号。
对于“音乐”这一词语,大家并不陌生。但它是否也属于象征符号呢?首先,我在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薛艺兵在《神圣的娱乐》一书中对音乐属性的六个层次的分类。一是音乐的物质基础(即发声器具),二是音乐的物理特性(即听觉器官对声波的感应),三是音乐的形态样式(即旋律、节奏、调性、调式等),四是音乐的艺术效应(即声音传人到人,引发的一系列生理、心理效应),五是音乐的社会价值(即社会个人或群体对音乐的认知、接受、评价等),六是音乐的文化归属(即每种音乐文化背景)。不难看出,这六个层次,前三种层次说的是音乐本身,其本身只是一种乐音的运动形式,并没有意义存在。但是,加人了后三种属性,当它能够与人内心的感觉同步融合,能被社会群体接受传播,能应用于脱离音乐聆听欣赏功能之外时,音乐刁‘具有意义。而这种意义的产生不是音乐本身固有的,而是被个人或社会注人情感或意义而成了用于意指目的的“符号”,正如梅里亚姆所说“音乐是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形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其中人们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及背后的文化都可以被音乐象征,被其符号化。
既然仪式与音乐都属于象征符号,那存在于仪式情境中的仪式音乐当然也具有象征符号的性质。所以杨小班鼓吹乐棚在丧葬礼俗活动中扮演着仪式音乐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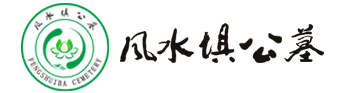

.jpg)

